谁也没有想到,就在推土机快要碰到墙体的时候,野庙的楼顶上突然出一个人。起初人们以为那是屋顶上突然冒出的一只动物,野猫,或狐狸什么的。
野庙是一座平房,平顶中央又加建了一层,既是上楼的走道,又是单独的储物空间,同时显得正中的屋顶高大耸立,超拔人世,有了宝塔的味道。这间房子楼顶边上,又留了个楼梯口子,上面又是一层,木梯爬上三层楼顶,可以俯瞰人间。
当人们看清三层楼顶那个活动的影子是个人的时候,人们惊叫起来,大声高呼,楼顶有人!楼顶有人!指挥的推土机的人赶紧说,停,停,推土机停下!轰鸣的推土机停了下来。人们都引颈朝上观望。领导发出疑问,怎么突然还会有人呢?不是说现场清理干净了吗?这是什么人?赶紧弄下来,不要半途而废。
这时,村里的干部从人群中挤了过来,对领导说,这是守在庙里的管事人,叫素姑,几十年一直呆在庙里。我们通知她拆庙的时候,她答应会离开,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偷偷溜回了庙里。看来今天的拆除得中断了,我们上去找了她,但她抱着门框说,如果我们上去,她就从楼上跳下来!今天要与野庙共存亡!
领导锁紧了眉头,说,不能随便中断,继续派出干部前往劝说!佛门不是自称慈悲为怀吗,拆掉旧村子,过了新生活,这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,怎么能够阻拦呢?
这时,素姑仿佛听到了领导的责问,开始在楼顶上大声地说起话来。素姑看上去是一个七十多岁的村妇,头发苍白,身材瘦小,但腰板依然硬朗,嗓门依然洪亮。她大声地指责乡亲们只顾及自家的房子,只顾着自己的生活,对野庙的消失不管不顾。
素姑滔滔不绝的演说里,是她所熟悉的每一家每一户许下的心愿。她一件一件地讲出来,仿佛在为庙前的村民翻读一本史书。她把实现了的心愿讲出来,也把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也讲出来。她把杨抗的心事讲了出来,也把马阿姨的心事说了出来,把朱骰家的心事说了出来。这些一桩桩事情,其实平时一直在村子里流传,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情,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,但被素姑突然集中到一块说了出来,让村子里人感到熟悉,又感到陌生。
素姑说的,其实这就是村子里一代代人的生死疲劳,生老病死,生生不息。村民听得有些呆了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座野庙的重要性。
他们现在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岁月。他们发现自己的打拼努力,确实跟这眼前这座不起眼的野庙有关。野庙是一条看不见的线,贯穿着每一户家庭的兴旺发达。他们远走他乡,他们荣归故里,他们白天劳碌,他们晚上休眠,他们出生上学,他们坐牢释放,他们红白两事,他们早出晚回,都被这座野庙注视着,关怀着,即使那些对神明不大恭敬的人,但他人的家事必然会传到素姑耳中。这些平常并不注意的人世沉浮,经由素姑慢慢讲道了出来,竟然有着非凡的意味,仿佛素姑果真掌握着人间的进程。
庙前一片静寂。连那位领导也在不断地抽烟,陪同的人一边听素姑讲说,一边不时观察几眼领导的表情。
素姑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布道。平时,人们各自沉醉在各自琐碎的生活里,奔忙着,吃喝着,痛哭过,嬉笑过,有了不顺就会到野庙里走走,特别是那些妇女,把家里的那点事情都跟素姑说了。但是说了之后,仍旧是各自的生活,人们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。野庙收纳着所有人家的悲欢离合。野庙从来不答应也不拒绝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心愿,为此能够一直平静地跟乡亲们相处。
素姑说,什么是神明?就是让你能够拥有心愿坚持心愿,并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实现心愿。不轻易答应你,但永远支持你。凡是没有实现心愿的,不要责怪神明不灵。有求必应,但不是有求即应。如果所有的心愿有求即应,这人间就会乱套。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。野庙最大的功业,就是能听得进所有人的心愿。素姑让乡亲们好好想想,将来每户人家都住上高楼大厦了,这当然是好事。但你们将来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,各种各样的心愿,这些心事如果在心里堵得久了,如果没有一座寺庙来承接,你们肯定会觉得难受!
素姑说,当初东山寺拆掉的时候,跟现在一样,没有人敢说一句话,但修建这座野庙的时候,大家不是背地里说了许多惋惜的话吗?这么快就忘了?!你们怎么能丢下庙宇不管了呢?刚刚闹完的庙会,大家的热情还没有散尽,平常你们热心前来诉说,现在又如何冷漠地任野庙拆掉?
素姑并不讲那些佛门经句,不讲那些阿弥陀佛,但她每一句话仿佛接通了村民的心电图。平时村民只知道,素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,是一个健谈的人。她能够和任何人细心地交谈,也似乎喜欢任何一个走进野庙的人。但她几十年来,只是默默地管理着野庙,撞响晨钟暮鼓,打扫落叶杂草,清除门户风尘,延续野庙香火。这座小城几十年轰轰烈烈地发展,最终都成为一种人间消息,传到野庙,传到素姑心里,又化为一种超然的目光。
素姑接着说起了野庙的历史。说起了多年之前擦子街的一场火灾,说起了一位红军战士藏匿野庙的故事,说起了野庙跟村庄几代人的恩情。
那时,擦子街还不叫擦子街。擦子街的杨家米店,是远近闻名的商户。那天半夜时分,米店老板杨和均醒了,不知道是内急,还是门外隐隐的敲门声惊醒的。杨和均的米坊就在老街东头,靠近村子的大池塘。
小城的东头有一大片宽阔肥沃的田野,叫七里段。这片流水段里出产的稻谷,饱满,芳香,成色好,是小城的粮仓。从擦子街流向小城和绵江的船只,再去往更遥远的州府。擦子街作为谷子的驿站,那些金黄的谷子走到这里,就要换一身洁白的衣服再出发。一家家米坊,一座座碾房,就是它们换衣服的地方。
杨和均家的小院,就有一座常年转动的磨坊。杨家米坊的规模在擦子街算是中等的,但杨老板为人好,和田东家关系不错,对那些送粮谷来的农户苦力也很温和很关心。杨老板对人好,也对谷子好,他知道这些粮谷来之不易,总是要伙计好好照看。杨家的大米为此颇有些名气。
那一天,杨和均刚为母亲做了大寿。来朝贺的亲友一拨接一拨,包括那些熟悉的田主和船家,总之是生意道上的朋友。这一天没有做生意。杨家米坊的大门关着,只留着一道侧门进出后院的居家之地。杨和均累了,雇请的堂侄这天也不当伙计,而是接待宾客的亲属。侄子招呼了一天也累了。
半夜时分,杨和均醒来头有点疼,是醒酒的后果。他爬起来,听到外头有急促的敲门声。不一会儿,感觉厅子里非常明亮。他穿起衣服来到厅子里,却发现不是天亮了,而是一片火光。那堂上的两支大蜡烛不知道何时烧完了,烛油铺满了木桌上的石板,从边缘往下淌,流到了地面,继续呼呼地烧起来,把木桌子完全烧成了黑炭,慈母的瓷像在火光中经受着锻炼,相框已经烧成灰烬。厅子里有一个天井,神案的火光点着了旁边堆放的寿礼,火光顿时冲向天井这个出口。
杨和均顿时头脑清醒过来,大声呼叫侄子起来救火。侄子不怕春寒料峭,提着水桶冲到后院边的池塘打水,一桶接一桶浇向神案,总算把火灭了。
杨和均庆幸火未成灾,突然想起惊醒自己的敲门声。他赶紧前往临街的大门,开门一看,却看到一名擦子,衣衫不整,喘着粗气,手里拿着一块大砖头,门脚上留下重重的磕痕。杨和均问,是不是你敲的门?擦子点了点头,却不开口,疲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。杨和均把擦子扶进了家里,让侄子准备了吃的,烧起火盆为他取暖。
擦子看到天色微明,急于离去。杨和均取出十块光洋送给擦子,但擦子不要,手里比划着什么。杨老板拿来纸笔,让他把意思写下,却是要老板为他准备一些米和盐。杨老板看到“盐”这样东西,不由吃了一惊,似乎知道了这个擦子的身份,按要求准备了一份,但看到擦子在地面一蹭一蹭地爬行,担心带着这些东西不便,于是就叫侄子帮他送去。擦子又写了一个地点,是野庙。
擦子走了,杨和均重新整理神案,摆好香火,有一些后怕。他对着香火喃喃念叨,感谢先祖保佑,如果不是擦子半夜敲门,杨家米坊将化成灰烬,万贯家财变成一场空。
这年春天,杨老板慢慢注意到,这个擦子经常出现在老街,虽然衣衫不整,但眼睛却格外有神。擦子似乎养成习惯,总是在黄昏的时候出现在村子里,总要在村子里绕一圈,最后就到老街来。杨老板似乎心照不宣,把擦子迎进家里,像上次一样重复馈赠之举。
有一天,方贵山晚上到杨老板家里买米,看到擦子在老街爬行,居民不时把一些吃食丢到他面前移动的一个破铝盆里。方贵山走得匆忙,没注意就把盆子踢翻了,擦子却没有生气。方贵山买米出来,看到擦子坐在米坊前,似乎等着他一般。方贵山说,别跟着我,我赔你一个盆子总可以了吧?方贵山在附近的商铺里买了一个盆子,转回来时却不见了擦子。
第二天,方贵山跟杨老板说起这事,杨老板说,这擦子是我家米坊的恩人,也是我们老街的恩人,如果不是他敲了一个晚上的木门,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,我家起了火灾,这老街火烧连营,大家都受难!
过了一些时日,这擦子一直没有出现老街。杨老板照样准备了东西,像供品一样恭敬地堆在神案边。有一天,杨老板听到石桥上人声喧哗,却是官军在桥上发号施令,请大家参观一颗头颅。杨老板挤了进去,听到那位长官在介绍头颅的来历。长官指着榕树,那头颅像一个葫芦一样高悬着,只是血肉模糊,看不清面目。
过了几天,杨老板突然被方贵山拉着往石桥走。这时天色昏黄,方贵山指着桥上一片洪水回流之处,说,你看那是什么?杨老板一惊,那水中翻滚不去载沉载浮的,分明是那颗挂在树上的头颅。
方贵山说,你知道这头颅是谁的吗?
杨老板说,看不清楚,我前几天现场看了也没看出来,难道伍子胥头颅唤起钱塘潮的传说是真的吗?这真是太神奇了!
方贵山说,你就是不关心政治,这事在小城都家喻户晓的了,听说这是一个游击队的一个大人物。我那天杀猪从小城卖肉回来,被官军拦住,要我去割一颗头颅。我不敢反抗,就去了。天啊,我一看到那尸身,却是一位多么挺拔的青年,但那面孔我至今忘不了,跟我在你家门口看到的擦子一模一样呢!
杨老板吃了一惊,说,擦子不是残疾人吗?怎么成了红军的大人物呢?
方贵山说,你没听到南面山中的游击队时常出没吗?他们时常化妆下山收集情报和食品,听说官军最后在野庙发现了一个联络站。这尸体从南山中抬出来的,原来放在杨家祠堂,乡民意见大,族长又来交涉,国民党军就抬到了东山寺。我怀疑那个擦子就是化装下山的游击队。说实话,我看到他的面孔时手有点抖动,但我又很快镇定下来,以免长官对我生疑。
杨老板听了更是惊讶,想到自己屡屡送赠的东西,心里有些惊悸,万一游击队出了叛徒,说出了联络点的事情,那就有杀头危险。杨老板对方贵山说,不管那头颅是不是擦子,他们都是同一个队伍的人物,因此就是我们村子的恩人,我们得厚葬了,我出钱你叫人,我们悄悄地进行吧!
桥头榕树下原来有个社公庙。杨老板后来每每想到那名牺牲的擦子,都想做点什么,就跟东山寺的主持提议,在这个河湾另建一座寺庙的附属建筑,就像龙珠寺一样,附属的庙庵有四五处,可收留一些走散的出家人。杨老板不但出钱捐建,而且还自己做起了庙会的会首。杨老板为烈士的牺牲悲伤,同时充满感激,如果烈士说出了提供的情报和食物,米店将遭到灭顶之灾。
“擦子街”这个名字,就是米店老板在主持庙会中形成的。开始,街坊邻居觉得名字不好听,无奈杨和均总是把“擦子”和“老街”两个词相提并论,“擦子街”最初有意无意的口误,传说越来越精彩,越来越神奇,人们便原谅了这个粗俗的名字,将错就错起来。擦子的传说让老街便显出岁月的沧桑。而故事中的人物越来越走向符号化。
随着岁月推移,杨和均所传说的那些事情没多少人相信。擦子到底是什么人,谁也无法确认,头颅是什么人,也没有人去追问。
文革时期,野庙的和尚走了,野庙成为真正的野庙,和尚公墓里有人竖起过一块牌子,写着“烈士纪念碑”五个字,后来又被人清除了。杨家米坊后人每年都会去祭扫,但杨老板走后,后人并没有热心地继承这个传统。最终无名墓地冷落了下来。后来,南面山中建起了烈士陵园,野庙就成为无人关注的历史。
素姑讲述这些的时候,是为了告诉村民要知道报恩。当然,素姑也讲起了这座村落当时是如何收留她的,仿佛以此让村民相信这些传说有着确切的来源。在最后,她衷心地表达了对村落的感激之情。她说,她希望这会是她最后的存身之所。
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4816号
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4816号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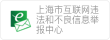

发表的评论审核通过后会在评论区显示哦~ 可在个人主页查看书评的审核情况~